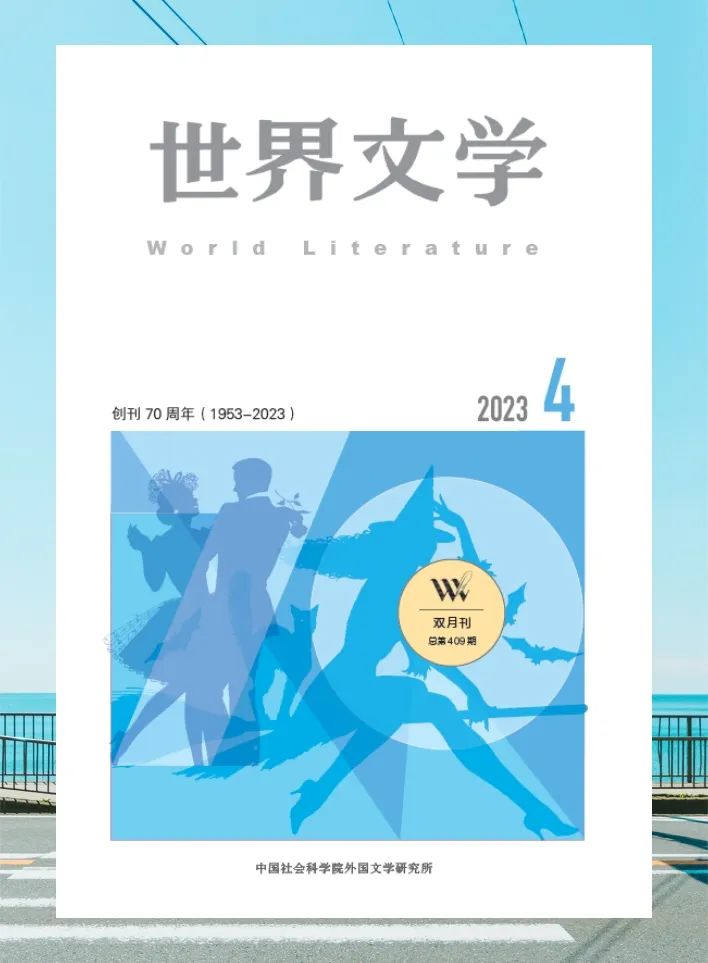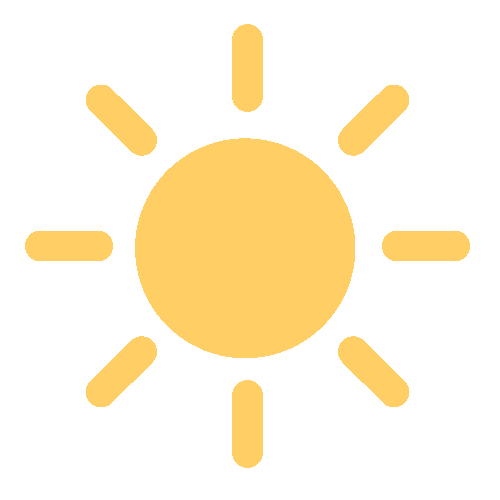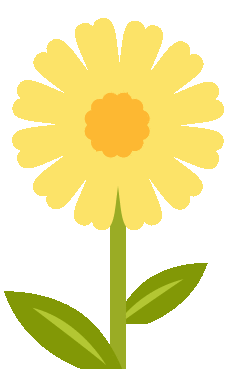周末文学|奥•比嘉•大城【秘鲁】:冲绳那闪闪发光的灰烬就这样碎裂了,在虚空中,在虚无里……

![]()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二十二年来,无论寒暑,哪怕身体抱恙或者疲乏不堪,她都会在同样的、抽象的下午,走完同样一段路。是的,这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是需要一板一眼遵循的仪式,在岁月的边界上,无止境地重复,再生,只为捕获并困住记忆。一分又一分,一秒又一秒,她都在对自己说:冲绳依旧在,依旧完好无损,将来也会继续毫发无损地存活在自己的记忆里,自她们儿时离开那里至今,从未改变。
奥古斯托·比嘉·大城作 刘犀子译
清晨六点,宫城奶奶【此处及后文中所有提到“宫城奶奶”的地方,作者使用的都是日语“奶奶”一词的拉丁字母拼写:obachan】睁开眼睛。她做了一个磕磕绊绊的梦,半梦半醒间,看见四周的墙壁和屋子里的椅子都跳起舞来,颇不真实。她等了一会儿,和往常一样感觉肚子里有一只冰冷的利爪。不知为何,她的心里腾起一种预感,怎么都刹不住车:十万火急!死亡要来了——就是今天,错不了的。过了好几分钟,她才定住神。这位徘徊在谵妄边缘的七十六岁老太太,要进入一天的日常起居了。整理床铺。换好衣服。在卫生间里愣了愣神。洗把脸。刷牙。接着又叹了口气,在镜子里看见一群早起的鸟。回到卧室,当街的窗子外面,正在下螃蟹雨【利马是一个干旱无雨的沙漠城市,几乎不下雨,宫城奶奶却看见天上像下雨一般落下螃蟹,一方面表明她精神状况不佳,无法摆脱幻觉,另一方面,据《平家物语》记载,死去的武士形态如蟹,仍在海底遨游,此处的“螃蟹雨”暗指宫城奶奶对日本战败史的记忆】,停都停不下来。宫城奶奶一言不发,一念未动,严正而悉心地谛听后头那间屋子里的动静:几个孙辈的孩子吃过早餐,出发去上学。除此之外,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是对此前每一天的精确重复。儿子吉酱没有一句抱怨,只是机械地完成拉开店铺卷闸门的仪式。这家杂货店位于乌安卡韦利卡大街【位于秘鲁市中心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途经7个街区,商业繁华】和安伽拉埃斯街的交叉口上。
简单吃过早饭,宫城奶奶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定,那是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摆了一条长凳。她神情严峻,不露声色,目不转睛地盯着店门,看着上午的顾客一个个走进来:撸起衬衫袖子的工人,喋喋不休的家庭主妇,晕头转向的路人……他们都住在这个街区,没错,就是他们,内心狡诈,表面上倒是客客气气,来买牛奶、黄油和香烟。吉酱和妻子富佐子负责招呼客人。美丽的富佐子是第二代【此处使用的nisei一词是源自日语的外来词,意为“第二代”,在秘鲁西语的语境中指父母是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日裔秘鲁人。这个词的日文汉字写作“二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词中“世”字包含了“世代”“时期”“时代”“世界”等多重含义】日本移民,待人亲切,对谁都是笑脸相迎。一波又一波顾客进进出出,只听见嗡嗡作响的说话声,硬币磕在柜台玻璃上,大勺子在装蔗糖的袋子里闷头挖着。九点钟左右,罗德纳斯来了,他是个司机。一瓶汽水下肚,他靠近宫城奶奶,无厘头地问道:“老奶奶,秘鲁总统是谁呀?”
她回答得很大声:“莱基亚!【奥古斯托·莱基亚(1863—1932),曾在1908年至1912年和1919年至1930年间两度出任秘鲁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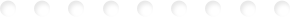

罗德纳斯哈哈大笑起来。“傻老太婆,”他说,“像是被关在别的世界里……”吉酱打断了他:“她在天上呢,跟那些神灵在一块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哄闹着,大笑着。这个上午不出意外地落下帷幕,安安稳稳,没什么波折。宫城奶奶依旧不为所动,只是盯着街道看:车辆行来驶去,路人形形色色,街角熙熙攘攘。恰在此时,她看见一束黄色的光划破天际,一队小海马凭空出现,不可思议地在空中跳起舞来,抖落一种细腻的尘埃粉末,然后消失,只留下海产的气味。转瞬即逝之物的消亡,再无回返或重复出现之日。宫城奶奶微微地笑了,像是从迷梦(又或许是超现实)中转醒,泪水如注——她可是从来不哭的呀。乡愁?也许吧。伤感?也有可能。对世界的告别?那可不是。
总之,在她昏昏沉沉打起盹儿的时候,像是忽然又能感知到时间和距离了,忽然惊醒,听见远方传来儿媳富佐子的声音,喊她吃午饭。她照做了,回到饭厅(兼仓库),不紧不慢地喝汤,吃蔬菜,不慌不忙地咀嚼米饭,喝桌上的茶。又过了一阵子,小女儿美酱到了,她是来换班的。宫城奶奶觉得自己的使命解除了,于是回到卧室,换上睡衣,睡午觉。
她做梦了。有一片荒原,下着雨,腾起令人难以忍受的蒸汽,各色气味,寂静。她寻得一只站在石头上的乌鸦。奶奶问道:“哪里能找到死亡?”乌鸦说:“此处有的是哀恸,是暗夜。”奶奶沿着蜿蜒的小径继续走,听见一头鹤的质问:“不平能得到匡正吗?缺憾能得到补全吗?”奶奶回答道:“永不。人生无法得到匡正。人生无法得到补全。”狡黠的鹤提醒道:“享受当下的这一天,不要相信明天。你会在荒野背后找到死亡。”奶奶继续走,没有路,攀援而行,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承受着痛苦、折磨和空虚。她受不了了,又渴,又饿,又冷。荒野却永无尽头。这时,她遇到一位时间守护人。“风暴正肆虐。”他说。就这样,奶奶在梦里等了二十年。她耐心地在下一个转角处等待着,遭遇了海怪,畸形的老虎,还有大得离谱的鬣狗。最后,在深渊的边缘,出现了一只蝴蝶,翅膀发光,它飞了起来,倏忽一瞬,随即就消失在空中,留下一串黄色的鳞片。


宫城奶奶醒了过来。粗重地呼吸。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说。都是些纠结的梦。她平静地坐在床上等待着,看着下午的光线穿过窗户。她站了起来,专注于自身,无休无止。力气回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她洗完澡,换上衣服,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收拾停当后,她走出门,朝卡涅特街走去,打算拜访自己的发小真荣城老太太。二十二年来,无论寒暑,哪怕身体抱恙或者疲乏不堪,她都会在同样的、抽象的【对宫城奶奶而言,记忆是具象的,现实反而是抽象的】下午,走完同样一段路。是的,这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是需要一板一眼遵循的仪式,在岁月的边界上,无止境地重复,再生,只为捕获并困住记忆。一分又一分,一秒又一秒,她都在对自己说:冲绳依旧在,依旧完好无损,将来也会继续毫发无损地存活在自己的记忆里,自她们儿时离开那里至今,从未改变。
宫城奶奶以这样的方式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坚定不移,每日逆着人流而上,游走在乌安卡韦利卡大街周围,同样灵活的穿梭,同样不散的倦意,同样难耐的焦灼。她会穿过乱糟糟的小巷,看见太阳底下晾晒的衣物,钻过几道苇墙,在拉奥罗拉市场周围一圈撞见白皮肤的混血人,也有肤色如乌鸦一般的混血人。不管用何种途径,不管什么目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街上的氛围多么令人丧气,不管她感觉多么无依无靠,不管她外国人的长相多么扎眼,反正现在她要走到明美瓷器店,跟柜台后的店员打招呼,然后走进店铺的里屋,去找卧床的真荣城老太太。她会把屋门关上,两个人面对着面,望进对方的眼睛,一边呼吸着积存的灰尘,一边就着简陋的油灯,共同回忆起泥泞的院子,竹制的窗户,一家紧挨着一家的瓦房,木制建筑的老书院,茂盛的榕树,名护【位于琉球群岛冲绳岛北部】的红土,冲绳半透明的空气里泡沫状的云,四面环绕无从摆脱的群山,还有永远不会躲进山谷的太阳。
就这样,在随后的三个小时(从来不多,从来不少)里,因过去的伤痕而生出的愁苦统统化作深不可测的天空,笑声,土路,蒸腾的气味,飘香的果实和童年的时光。她们无休无止地沉浸在回忆当中,心情澎湃,无法自拔。有时候,记忆如同一管盐水试剂,一段无关紧要的情节,一次无人认领的事故,经过上百次重新编造、夸大、变形,重又浮荡在那间昏暗的卧室里,闷不透风,仅有一盏灯微弱的亮光。半身不遂的真荣城老太太斜靠在床头,听着对方惊惶的语调,那不只是声音,更是漩涡状地奔涌而出的怨尤。
曾几何时,她们一起上学,一起乘坐乐洋丸号横渡重洋,一起在利马安家,跌跌撞撞,一刻也不得松劲儿。她们都被安排给日本男人结婚,毫无情调,无风无雨。丈夫们把旅馆、粮油副食店、理发店和木匠铺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而她们在生活的涡流里匆匆生儿育女,把自己的光芒投注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那都是粗重的活计,牲畜一般,日复一日的折磨,没有片刻休息。再无其他可能了,她们就这样藏在布雷尼亚、里马克、乔里约斯或塞尔卡多【这些都是秘鲁首都利马的街区名】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还要在店里招呼那些给我们带来多少屈辱的土生白人和印欧混血人”),得不到丝毫同情,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喘息之机,直到世界末日。就像,石头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撞在地上裂成几块,再被碾碎。没人哭泣,没人害怕。她们便是如此,在岁月的褶皱里,虽偶有旁逸斜出的时候,但终归是留在了这浓稠的寂静里,在遗忘里,在沉郁里,也无懊悔,也无恸哭。命运使然,宫城奶奶在拉奥罗拉市场附近重新遇见了真荣城老太太,由此她们便恢复了儿时雷打不动的每日相聚,在那个逼仄的昏暗房间里,执迷于追忆往昔的惊骇与欢乐,让那个抛下了她们的世界重又浮现在眼前。直到宫城奶奶说得筋疲力尽,大脑一片空白,时间恰好是下午六点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她才向真荣城老太太道别。


回家的路和去程一样,她对路上的人、房顶以及老旧的木栅栏瞟都不瞟一眼,只顾着想自己的心事,全神贯注,反复回味细节,兴致勃勃,感觉像是被一股力量推着往前走,呼吸着街头巷尾刺鼻的空气。就这样,她回到店铺,跟儿子吉酱打了招呼,和小女儿美酱换了班,走到饭厅(兼仓库),机器似的停留在孙辈身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大笑、玩闹、沉迷电视,一如往常。宫城奶奶坐在自己靠墙的椅子上,对噪音完全免疫,对那些家长里短的讨论也置身事外,继续在货物、大米、货架和自己的呼吸之间,专注地回忆着那粘附在墙上的流金岁月。她的过去,她的现在,她的未来,都在那里了,它们旋转着,像一条密封在胶囊里的蛇,和孙辈的吵闹以及电视机里的幻象混在一起。
她可以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上好几个小时,甚至打个盹儿。不知怎地,也不知为何,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那个突如其来的中午【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突袭珍珠港。这一事件在秘鲁引发了反日暴乱,造成数百人伤亡,600间日本商铺和住房被破坏,损失达700万美元】,日本引爆了太平洋战争。“当时空气中充斥着火药味,但我们并非没有准备,我们从来不是毫无防备的。人群怒气冲冲,他们终于找准了报复的时机:‘等着瞧!’在利马,我们必须如此面对命运,遭到排斥,孤立无援。”鼓声四起,骂声震天,她和丈夫藤吉还有四个孩子躲在里马克区一个小屋的角落里,惊恐不已。邻居们朝杂货店扔石头,打破窗户,往里面吐痰,还大肆打劫。到处都是抗议集会,他们看见有人举着秘鲁国旗经过,辱骂声和叫嚣声不绝于耳,却没有一个日本人走上街头。他们已经习惯了无动于衷,经年累月地垂着脑袋,因为那些都不重要,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源,无处求告。宫城奶奶坐在椅子上,背抵着墙,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孙辈,一边回忆起往事。晚上九点,这一天无惊无险地过去了,宫城奶奶眨眨眼睛,有些困倦了,迫不及待地遵循每天的常规移步到卧室,一如往常地铺好床,换上睡衣,拜一拜佛龛,躺下了。
而后,在入梦时分,众多鬼魂出现了。那些战争中的日本逃兵——秀永,新垣先生,西村兄弟——手足无措地躲进利马郊外的农庄里,想要与世隔绝却被警察四处追捕,百般凌辱。她又想起另一些人,秘鲁当地的老大粗,皮肤黝黑的印欧混血人,还有看着像桑博人【指黑人和当地印第安土著的混血】的家伙,那些短袖打扮的骚乱者不停挑逗乃至凌辱手无寸铁的店员。她回想起他们打劫了自己在里马克的店铺,是的,他们抢走了、毁掉了一切,绝对意义上的一切:架板,货物,甚至连睡觉用的木台、衣物和家具都没有放过。彼时的苦痛她永生难忘,从未平息,哪怕如今深陷时光的泥沼,潜意识里那种深切的痛还是盖过了羞辱和怨恨的滋味。梦境里粗糙的画面,一张张脸孔,决绝的动作,层层叠影,在长夜将尽的时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宫城奶奶在清晨六点醒来,发现自己在卧室里,像是一如往常,却又仿佛前所未有。她死死地盯住天花板。梦的潮水退却了。衣柜在,佛龛在,小圆桌也在。她感觉到肚子里冰冷的铜块。预感的声音响起来了:十万火急!死亡要来了——就是今天。她去卫生间洗了脸,对着镜子,看见了一九三四年的太阳。回到卧室,她听见鸽子咕咕叫,还有螃蟹雨从窗玻璃上滑落的声音。内心毫无波澜。等她来到饭厅(兼仓库)时,孙辈的孩子们已经走了。儿媳富佐子给她倒了牛奶。两人说了几句话。吉酱七点半打开店门。过了一会儿,宫城奶奶也就位了,坐在柜台后面的一条长凳上,面朝门口,看着客人们进进出出。一成不变的生活。持久的耐心。莫拉雷斯女士来了,还有急性子比森塔。加斯帕尔哼了两曲难以入耳的华尔兹,要了一包饼干。吉酱殷勤地招待着,微笑,闲聊。富佐子在仓库里拣拾着货物。而宫城奶奶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老样子,心不在焉,一动不动,疏离得很。苍白的光线在店门前流转。街上车子发出噪音。圣卡洛斯巷的孩子们来了。
而她,宫城奶奶,从四个小时前开始,就被属于自己的那个一九三四年的太阳晃了眼睛。那是第四个月份里的第四天,在鲤鱼旗节上,出现了一个橙色又仿佛是绿色的太阳。当时有人对她说:要不怀爱意地等待,不要有希望。那是在冲绳的名护。过了三年,她远渡重洋,抵达,安顿;看见陌生的黑人,没有屋顶的房子,不知晓名字的土地和太阳。她就这样停留在世间一切变幻莫测的边缘,总是同样无动于衷的表情,小孩子一般,像是对什么都不在意。她没有出路,没有喘息之机,毫不热切,随便置身哪个角落都无所谓,就这样,她在布雷尼亚、里马克、乔里约斯或巴里奥斯阿尔托斯的某个小店铺里永远地迷失了。伺候丈夫,养育孩子,家务事繁重不堪,还要招待蠢笨的顾客。她有时热情,有时冷淡,总之是做了自己最懂得做的事情:顺应命势。不明白一切怎样发生又为何发生,不过,呼吸、行走、挪动胳膊就足够了。如今,站在岁月的尽头,玄妙莫测的宫城奶奶重又找回了那个太阳——柠檬色的,绿色的,也可能是橙色的。柜台后面的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心无旁骛,无动于衷,那个太阳就在她的眼底,像一朵花似的沸腾着。她兴奋极了,却能够自持,面无表情地抿着嘴唇,不发一言。
到了中午,儿媳富佐子招呼她吃饭,宫城奶奶只得抛下安宁的梦境,走进饭厅(兼仓库)。在饭桌上,她咽下蔬菜、米饭和菜豆汤。快吃完的时候,她盯着一只大黄蜂在空中盘旋着、盘旋着径直跌落在盘子里。那一刻,她决定了。救不回来了。她双手平稳,表情平静,走进卧室,找出自己最好的衣服,仔仔细细地洗了澡。在镜子的忧郁中,她看见了一道彩虹。螃蟹雨。她穿上衣服,扑了粉,最后,走向佛龛,上香,敬拜。这是二十二年来的头一遭,她改变了时间表,没到下午三点就出发去找真荣城老太太了,要去给她讲讲一九三四年那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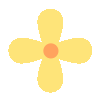

她走上街。乌安卡韦利卡大街兀自繁荣。面包店,药店,名古家的酒馆,朝着四方蔓延的小巷,三岛先生的店铺。宫城奶奶过了马路,把各式各样的院落、窗户、抢道的小汽车都甩在身后。她就这样决绝地走着,不再受乡愁之苦的纠缠,只被那一个念头推动着。在卡涅特街拐个弯,拉奥罗拉市场的熙攘扑面而来:摆摊儿的,卖土豆的,还有三轮车。到了明美瓷器店,她向店员问好,随即走进里屋,来到真荣城老太太的卧室。宫城奶奶在椅子上坐下,问了问对方今天怎么样。真荣城微笑着跟她打招呼,比比划划的,表示想听她说话。店员上了茶。
就这样,没有任何过渡,在逼仄的昏暗中,宫城奶奶艰涩的声音响了起来。就这样,在她鼻息的急喘中,无数条道路枝蔓横生,从遗忘中浮现,过去疯狂地奔涌,不加节制,幻化成一个个名字,一个个已逝之人的傀儡,奋力生活着的鬼影,灰烬遍天,烈焰。少年仲村渠出现了,羸弱,像一只小兽。那是在学校的院子里,一九三四年的鲤鱼旗节,群鸟立于藤蔓,大地收获果实,岁月一成不变、寂寂无名。那是名护,是那里的红土,是水泥厂的气味,一家紧挨着一家的瓦房,灰扑扑的自行车,刻漏【即水钟,一种计时工具,通过塔楼里水槽滴漏的水量来计时】,窗外啸鸣的风。那是冲绳,是那里温软的海沙,是芦苇地,烤红薯,南下去那霸【位于冲绳本岛南部,是冲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旅途,茄子地,如黛的青山。还有那个幻影般的球体,绿色的、橙色的太阳,在大雨中破裂。粗蛮的少年仲村渠说道:“别幻想了。等着吧,忍着吧,痛苦就是一切。”
后来,一九四四年还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她在中央市场附近又看见了仲村渠,他瘦瘦的,说话做事荒腔走板,举止粗鄙,让人难以忍受。原来,他也远渡重洋,定居利马,学了一套装腔作势的功夫,显得神秘又大胆。“纳坎达卡里克”【纳坎达卡里克(Nakandakarique)是日语姓名“仲村渠”(Nakandakari)按照发音用西班牙语拼写的结果】自战败的灰烬中走出,途经北部地区帕拉蒙加、苏佩或瓦乔这些地方的庄园,最终流落在中央市场,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帽子耷拉着,遮住半张脸。他没有幻想,不抱希望,和一个当地的印欧混血女人纠缠不清。总之,蛮汉仲村渠在中央市场摆摊卖起花来。大家都管他叫尼古拉斯——日本人尼古拉斯,流浪来的,古柯叶嚼个不停,爱玩骰子。而在宫城奶奶心中,曾经的那个世界依旧存在,执拗地继续旋转着,无法摆脱,没有宽恕,没有爱,没有遗忘,如同太鼓的隆隆声,总是一次又一次响起,不为外物所动。
至此,激动不已的宫城奶奶已经筋疲力竭,她停了下来,不再吹灌往日的烟云了。整整三个小时,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当然,她体内的生物钟还是能觉察出差别,现在是下午五点。不是六点。她的心头浮现出一丝恐惧,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和往常一样。她道了别,离开店员、柜台、瓷器店。她提起脚,踩上卡涅特街,和来的时候一样决绝。
在黄昏时刻熹微的光线里,她端详着老旧的商业设施。贯通的市场。卖土豆的摊子,推独轮车的小贩,卖南瓜的。人来人往。在她失控的大脑里,街巷扭曲,狂犬吠叫,天空呈现出奇异的颜色,醉鬼的脸也变了形。她不为所动,一股脑地走下去。就在她拐上乌安卡韦利卡大街的时候,一辆卡车飞驰而出。宫城奶奶没有看见。撞击。她感觉自己被抛到空中,然后狠狠地落在地上。她还有意识,并不震惊,也没有幻想。先是遗憾,紧接着,是无尽的狂怒,因为,冲绳那闪闪发光的灰烬就这样碎裂了,在虚空中,在虚无里……


作者简介

奥古斯托·比嘉·大城(Augusto Higa Oshiro, 1946—2023),秘鲁小说家,著有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回忆录和四部长篇小说,曾受到秘鲁文化部的嘉奖。比嘉的父辈是来自日本冲绳的移民,最近二十多年,他致力于用西语创作在秘鲁的日本移民及其后代的故事,尤其关注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方面的主题,连续出版了《中村嘉葎雄的启蒙》(La iluminación de Katzuo Nakamatsu)、《冲绳依旧在》(Okinawa existe)和《外人》(Gaijin)三部该题材的虚构作品(集)。在比嘉看来,书写秘鲁日裔社群的历史与现实是“一种个人责任”,因为“我是日本移民的后代,我有义务在写作中聚焦这一主题”。
《冲绳依旧在》选自圆桌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是比嘉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来自冲绳的第一代移民宫城奶奶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作家采用语词重复的修辞和平行回环的结构,搭建出虚实呼应的叙事空间。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起居中,回忆与幻觉掀起惊涛骇浪,宫城奶奶对个人和集体记忆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缩影。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3年第4期,策划及责任编辑:汪天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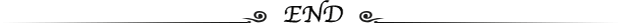
点击上图,订阅全年《世界文学》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
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3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