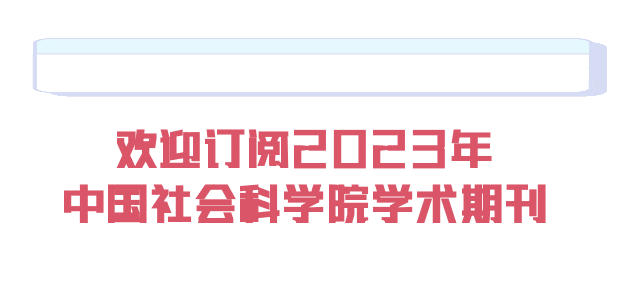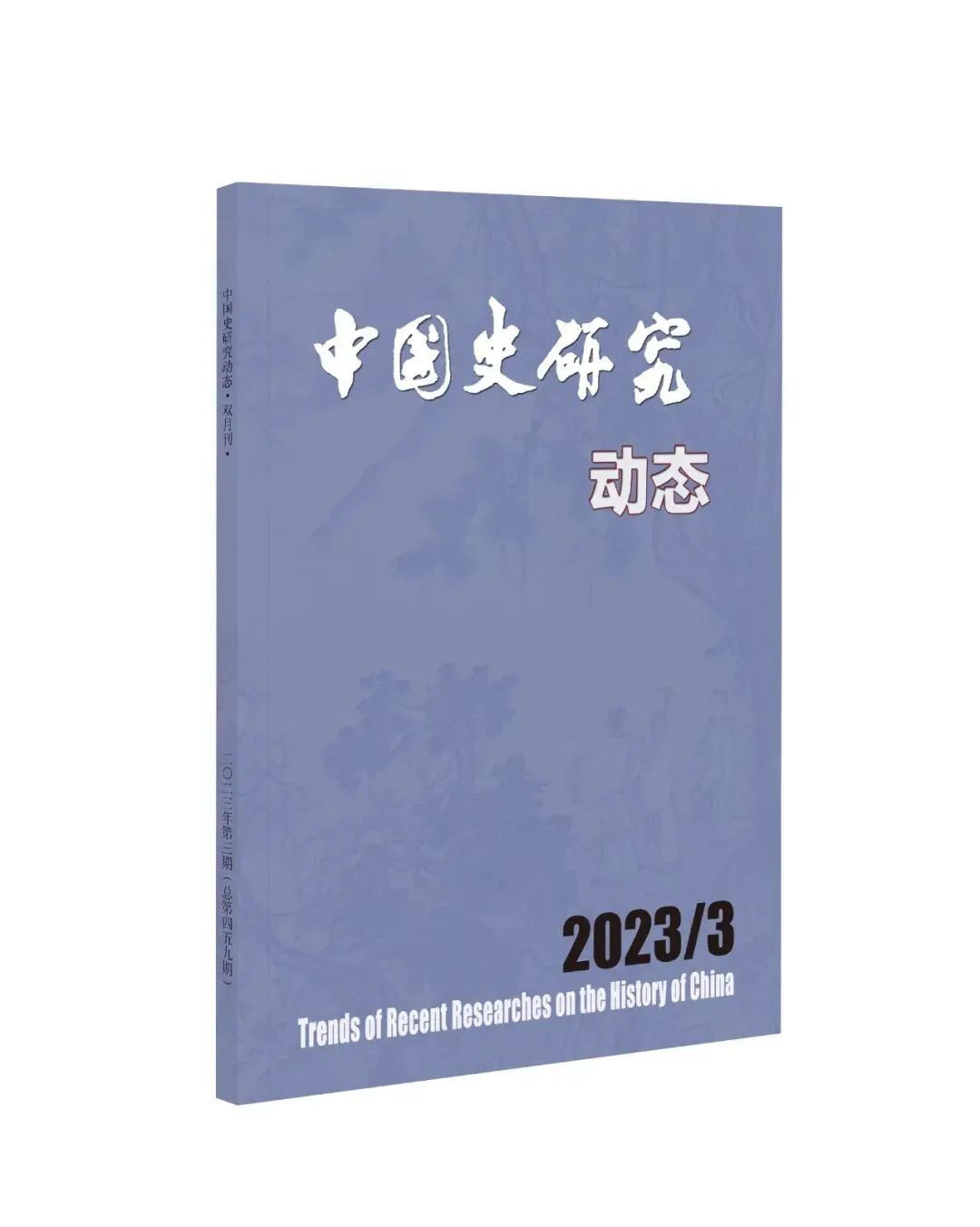精选文章丨笔谈: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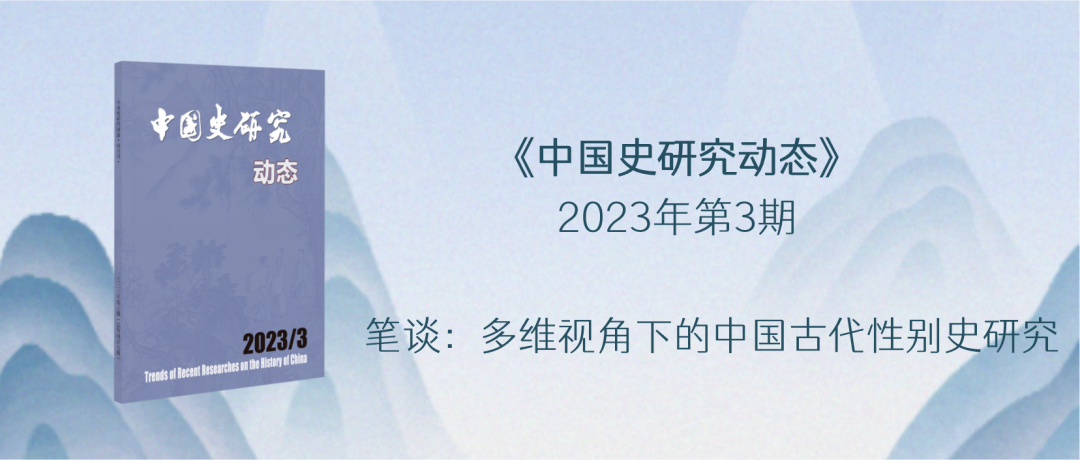
·笔谈: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
编者按: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兴起至今,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随着学科发展,国外史学观念的引入,又衍生出了性别史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已有研究的视野和深度,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内涵。在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多的背景下,学科发展似乎未能随之出现质的跨越,一些亟待厘清的问题,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为此,本刊特邀数位专家学者,从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多个方面,展开总结与反思,以期从更多的学术维度,拓展并深化妇女史/性别史研究。
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为何略显沉寂?
李志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在中国学术界称妇女/性别史为“显学”,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尽管人们或对相关研究的水准有不同评价。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妇女史研究兴起;90年代,“社会性别”理论被引入,性别史研究兴起。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独立的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宋少鹏《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5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妇女/性别史异常活跃,引人注目。
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妇女/性别史似从繁盛走向了沉寂。但其实,研究的“量”并不支持“黯淡说”,以中国古代妇女/性别史为例,2011—2020的10年,刊发的论文数量达2500余篇,著作也有140余部(数据统计方法见李志生、王丹妮《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综述(2011~2015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11~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而2000—2010的10年,刊发的论文仅数百篇。
“量”不成问题,那就在“质”上了。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中存在着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是研究内容呈现“分离领域”倾向,缺乏两性视角关照;二是研究的“碎片化”偏向明显,缺少宏观意识;三是提出的方法多,但对理论的理解不够(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陈雁《当妇女提问时:新时代的妇女史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李志生、王丹妮《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综述(2011~2015年)》)。问题提出了,如何看待与解决它,就是当下之急了,因为关涉到学科的发展与走向。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中古妇女/性别史研究现状,并结合个人体会,略陈己见。
一、关于“分离领域”倾向
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路径,大体在添加史—她史—社会性别史的三阶段,现在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主要还维持在“她史”阶段,且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妇女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故挖掘女性历史轨迹的“她史”,其实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起点,学人们着意于在历史中发现妇女、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他们的这些研究,都将为深化历史认知、将妇女纳入性别考察框架,提供有益的先期积累。
但仅止于“她史”,并不是妇女/性别史追求的目标,书写出两性的大历史,才是学人们念兹在兹的宗旨。琼·斯科特(Joan W. Scott)提出社会性别理论(Gender),初衷虽在探讨女性的性别建构、追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社会建构者的男性,同样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起点。自古以来,有社会就有男女;同时,社会塑造的也不止是一性。像在人们的通识中,贞洁是妇女受压迫的重要面相,但中国历史上对男性同样也有贞洁要求,只不过较妇女宽松而已。所以,不汲汲于妇女一性的历史,打开两性观照的视野,或许会对男性压迫、男性建构之类的话语释然很多,也会以更平和的大历史观重新审视历史。早在2002年,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就指出:“一些妇女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种两性对抗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抗论却是违背事实和逻辑的”;“不少妇女史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此番直言,切中了中国妇女史难以迈向性别史的症结,也点出了妇女/性别史难以融入主流学术的原因。
一项研究显示,在1975—2015年间,在美国历史学界最受欢迎的史学方法是妇女/社会性别史和新文化史,而2015年,妇女/社会性别史更是研究成果最多的单个领域(Lynn Hunt, History: Why it Matters? Polity Press, 2018)。但这众多的研究成果,却并不一定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性别视角变成了主流学界吸纳的概念和工具。面对这种情状,美国妇女/性别学界早有人担心,“妇女与社会史领域可能不再属于它自己……”(Rebecca Edwards,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in Eric Foner & Lisa McGirr eds.,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但这种两性的而非女性主义的视角,其实与中国的价值观更契合,相对于女性主义发达的美国,我国历来强调两性和谐,因而,性别成为研究视角而非过分强调妇女的特殊性、妇女/性别史走出一性的局促、迈向两性的和谐,在中国应更为可行。
至于具体研究方法,以新译的《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詹镇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为例。该书的作者高彦颐是海内外妇女/性别史研究的重磅学者,但在她的这部著作中,女工匠顾二娘却隐身到了清初工匠的大历史中,虽然如此,顾二娘于此书的意义却非凡。在该书中文版“自序”中,作者谈到选题时说,她写作的初衷就是要考察女性物质文化,但多方搜讨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最后成了我的‘真命天子’”,顾二娘才是作者展开这一论题的导索(尽管高彦颐私下交流中也承认顾二娘的史料相对欠缺)。不但如此,该书始终贯穿着性别视角,特别是最后的结论部分,更有对“文匠的性别问题”的定焦。
所以,对于性别历史,我们必须直面操纵古代社会运转的是男性的现实,运用女性视角固然可以观察到妇女的丰富世界,但妇女世界是依托在男性政治社会基础上的,则毋庸置疑。举例来说,安史之乱前的崔暟家的妇女们,平静地生活在东都洛阳,虽然她们每人有乐也有苦,相互之间还有不睦,但安史之乱的烽烟,使颠沛的南逃成了这些妇女无可选择的命运,她们的喜怒哀乐甚至生死,都被笼罩在这一政治事件中(李志生《唐崔暟家妇女的日常生活——基于性别视角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常建华、夏炎主编《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科学出版社,2019年)。所以,像高彦颐《砚史》的研究方法——将妇女置于大历史中,但带上性别的视角,或许是我们放下执念的妇女、直面两性历史的一个可行思路。
二、关于“碎片化”偏向
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也是深化史学研究方法的议题之一。“碎片化”倾向(与微观史学紧密相连)并不止表现在妇女/性别史研究上,它也是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话题。学者们对“碎片化”研究的批判各有所重,“综合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一致,都要求摒弃细碎的结论而愿意接受零碎的证据”(黄若然、安子毓《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
“碎片化”研究是必要的,“前些年西方流行的‘微观史’……是以可分享的个体生活‘经历’来颠覆被既存论说抽象出来的整体历史‘经验’。其所针对的,正是更早那些众皆认可的宏大叙事”(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像唐代山东士族出身的郑琼,嫁给了关中士族新科进士杨牢。对于唐史,陈寅恪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唐后期,山东士族在文化上的心理优势,让他们睥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的众生。然而,在郑琼与杨牢的婚姻中,郑琼高门背景对她却是一种束缚,这就促使我们从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唐后期的社会分层问题(李志生《妇女的自我感受: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碎片化”研究也在反思史学的“科学化”,忽略“人们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日常经历”,就无法了解人们的真正“需求”,也就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Alf Ludtke, translated by William Templ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rinced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碎片化”研究的问题小,但要求的功力并不低。荣新江对唐代女扮男装的考察是一个典范研究,作者对唐代女扮男装的流行时间、出现原因、背景和性别意识,作了详尽而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作者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熟稔和对宏观背景的把控,更令人印象深刻(《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在这一强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或可再放宽视野,那就是在唐代还有一种女扮男装为“服妖”的正统观念,而这一观念还贯穿到了唐初的正史修纂中。现实与理念的并存不悖,其实才真正体现了太宗所奠基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治国理念(李志生《唐人对女着男装为“服妖”说的接受史》,《唐史论丛》第31辑,2020年)。这一推进,得益的是史学史的研究。唐代女扮男装研究还提示我们,要对史料保持高度警惕,某种史料——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正史,透露的或只是历史的一个面相。爬梳史料、文本考察、勾连史实、由小见大,无一不是“碎片化”研究的前提。
说到对史料的警惕,它一向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大议题。受后结构主义影响,文本研究(或称史料批判、历史书写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内容,考察史料书写、递嬗中的性别意识,素来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对史料的警惕绝不止于此,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正史与笔记小说,甚至各个墓志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形成方式、相异的受众群体与传播渠道,这又都会影响到史料的多寡和结论的得出。再回到女扮男装的问题,荣新江主要基于所爬梳的壁画墓图像材料,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天宝以后,女扮男装的现象立刻消失。”(《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但齐东方的研究显示,唐代前后期的墓葬本身就发生了变革,后期丧葬中,地面丧祭地位提升,地下墓葬则变得简陋(《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这是否影响了唐后期壁画墓的修建与数量?再有墓志,田安通过权德舆撰写的两方亡女、亡孙墓志,提醒中古墓志的阅读者,墓志撰写者“敏锐地意识到纪念传记存在多种多样的潜在读者”,因而对撰写的墓志内容多有选择(伊沛霞等主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因而,无论何种材料,背后都隐含着时代、阶级、性别、人生阶段、种族的话语,所以面对史料,“与其将‘文本分析’抑或‘史料批判’看作研究方法,不如将这种研究手段当作学者解读史料应当恪守的‘自觉’”(吕博《武汉大学“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简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
三、关于理论的深化与运用的可行性
20世纪末中国妇女/性别史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本土妇女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学术潮流的推动,学人们认识到,立足本土,以西方理论打开思路,是一条有效的研究路径,因此,性别史、日常生活史、情感史、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纷纷被引入,大大丰富了研究内容。与此同时,对理论理解不深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许多研究将理论变成了引人的标签和罗列的概念,并未真正达到引导思路、开拓视野的目的。
兹以情感史和日常生活史为例。近年来,情感史是笔者在课堂讲授的重点理论之一,情感史和性别史几乎同时兴起,“妇女是感性的动物”这一传统认识,又使两者产生了天然亲近关系。情感史探讨的是社会的情感规则和集体或个人的应对,针对的是理性史学中存在的偏颇,情感史与性别史联手,“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挑战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王晴佳《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史学集刊》2022年第3期)。在教学和阅读时笔者注意到,虽有若干声称情感史的论作,但实际谈的都是个人、群体的感情,而非情感史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在2022年5月举办了“路径与取向:从情感史视角看中国历史”的讲座(论文见李志生《路径与取向:情感史与中国古人情感》,《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听者踊跃,这或许正是年轻学人希望深化理论学习的体现。
相较于性别史和情感史,日常生活史兴起得更早,它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日常生活史针对的是史学“科学化”的“见物不见人”,研究的定位是“目光向下”。就中国而言,帝王将相曾是传统史书的中心,也是霸占早期研究和近年荧屏的主角,因此,“目光向下”地将研究定位在下层妇女,当然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最理想的结果。但这一诉求关乎史料的多寡,史景迁可以写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的经典著作,是因为王氏生活在17世纪,作者有包括县志、个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的多种材料可以使用。但中古史不同,有时预计的主题是下层妇女,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皇权,这就是史料限制的结果。
就中古妇女日常生活史而言,定焦下层固然是至上追求,但“目光向下”的难度大。如此,发掘史料就是关键一环,新史料当然令人振奋,但旧史料也依然蕴藏着诸多待发之覆,只不过需要变换思路进行思考;对待选题则是另一关键,从学术角度讲,直面史料欠缺,在暂时无法达到“目光向下”时,探讨上层也不失为一种策略,这并不意味着学术视野不够。其实,上层也好,下层也罢,只要史料允许,题目又能发掘未知历史、补充甚或修正大历史,那就是深化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有益选题,而这也正是笔者近期将目光投向虢国夫人日常生活的原因(《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
关于妇女/性别史研究的理论运用,对拓宽思路、整合问题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理论的运用必须基于本土、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先对理论有深入理解,避免使其沦为彰显时尚、吸引眼球的幌子。
性别史研究反思及拓展的两个维度
陈 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性别史的概念范畴与研究的理路、视角方法在学界集体的反思中不断深入与拓展。近两年,笔者因参加《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中的“《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项目,开始接触唐代妃嫔册封文研究等涉及性别史论题的研究,兼之由本来从事的先秦两汉文学跨度到唐代文学领域,围绕性别史的断代史、利用出土新材料等相关问题,由此生发一系列的学术性思考。以下拟从旧传统断代史、新材料出土文献的角度,浅谈几点认识与想法。
一、断代史与性别史
纵观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女性往往被著书立说的男性史学家们所叙述的主流历史所忽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西方引入社会性别(gender)这一重要的分析范畴而逐步本土化(参见杜芳琴《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性别史的研究视角继之进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性别”是一种对传统研究视角与观念的全新挑战,“史”则显然无法摒弃和割裂旧有的史学传统基础。反观史学传统,中国以朝代更迭式演进的漫长古代史,其编纂正史“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三史皆为断代史,断代史是我国古代史学重要的学术传统。从学界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早期妇女史进行简单填补女性历史缺位的“妇女添加史”,还是后来转向社会性别关系的历史叙事与研究,断代史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书写传统,极大促进了性别史的发展。
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史的断代史作品,主要有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赵东玉《从男女之别到男女尊卑:先秦性别角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美〕姚平《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王子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增订本)》(初版于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再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马珏玶《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以及由陈高华、童芍素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妇女通史》(杭州出版社,2010—2011年)所囊括的断代史部分著作等,成果丰硕而不胜枚举。
探讨性别史的断代史研究,需要厘清断代史、历史分期与断代这几个基本的概念。对此,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史学方法导论》,中华书局,2015年)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比较与分析:“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于情甚合,于学甚便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其观点强调了历史分期的合理性、必要性,指出历史分期与朝代更迭为限的断代史存在着联系和区别。
历史分期是研究史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属于一种特殊的以时间顺序为标尺的分类,旨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别,并从中发现其发展特点及规律。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主要有学习西方进化史观的“四分法”(桑原騭藏《东洋史要》)、“三分法”(内藤湖南《支那论》)、20世纪40年代高校广泛通行的中国历史断代讲授法“六分法”、新中国成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的分期,以及诸史家批判性接受主流分期法并结合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特点,来构建各自的通史著作体系。性别史属于专题史,专注于研究历史上人群中的性别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对于性别的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如果以性别史来分期,由于历史观及历史思想所产生的标准不同,必然会有不一致的分期结果。因此,性别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军事史等专题史的历史分期,会呈现出判然有别的分期结果,甚至仅就性别史而言,不同的学者分期结论也不尽一致。
断代是较为纯粹的年代学定位研究,而断代史则是某个具体朝代在横截面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表现与史实,与通史对立。不同时代的性别史研究,进行有机地统合才能形成纵贯的性别通史。通过相邻断代特征的考察进行一定的归纳与合并,辨析出量变到质变的分界,从而划分出主要特点相异的阶段,就是性别通史视野下的分期。其与各断代的性别史不是一个概念,也是单个断代的性别史无法体现的宏观面貌。
以时间为限度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傅氏所言“便于学者”“于情甚合,于学甚便”的合理性,断代史的情形与此相类。性别史的断代史研究者,充分利用断代史便于进行研究的特点,与此同时,对此也充满着反思与焦虑。马珏玶《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绪论》写道:“今天看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个凝固的整体,任何分割的方法都会带来人为割裂的研究风险。但是,作为单本的研究书籍,笔者无力做到纵贯古今。”
美国当代妇女研究的开拓者琼·凯利—加多的《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对性别史的历史分期有如下论述:“历史分期在妇女史中有希望发挥更好的作用在于,它已成了一种关联的历史。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做的,通过审视同一社会发展看到造成一个性别进步的而同时压迫另一个性别的社会机制上的原因,妇女史便与男性史有了关联。以此方法处理传统历史分期的概念,只要它们涉及社会主要的结构变革,就有理由、也应该保留。但在评价这种变化时,我们需要考虑它们对妇女和男人的不同影响,我们现在预料这些影响可能非常不同以致成为互相对立的,而对这种对立是可以作出社会性解释的。”(第86页)“任何对社会制度的研究都应包括对社会制度所塑造并蕴藏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我的新的历史分期的概念反映了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对历史变迁的评价。”(第91页)虽然此观点论述早期妇女史研究观念中的两性关系,尚属于相互压迫与对立的不平等关系,但她在这里强调历史变迁中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应该是决定性别史历史分期的关键性因素,值得引起重视。
传统史学的断代史及历史分期,易于出现强分时代而割裂历史的弊端,并一直受到史家的批评与反思。宋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1987年)云:“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编撰两部通史《白话中国史》《中国通史》及多部断代史的近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先秦史·总论》(中华书局,2020年)中称:“今之治国史者……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郑氏指出“无复相因之义”,质疑断代史割裂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吕思勉所论“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强调历史分期应以史事为中心。传统史学的诸多反思,对性别史的断代史研究也有积极借鉴意义。
性别史所聚焦的社会性别关系变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脉络,并非朝代更迭的断代史所能精确地同步分裂与隔断,因此,在断代史基础上进行叙述、讨论和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的性别史,应该充分考虑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点,合理地利用历史分期来讨论性别史有关的问题。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前言》对此进行清醒地反思:“本书将分殷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三章叙述。文化发展演化的阶段和时间的划分并不完全同步,所以有些材料的处理不能一刀切,而要兼顾描述的方便特别是事情本身的关联。”
性别史存在两个具有相互对应关系的研究范畴,即很多学者所讨论的共性与个性或整体性与差异性的问题。女性具有群体的共性特征,也因不同种族、民族、阶级、地域、时代、宗教及个体之间而存在着极大差异(参见高世瑜《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考察性别史所关注的常见主题,包括两性婚姻制度、妒妇现象、才女文化、妇女贞节观念、女性财产权及继承权、女性参与政治等。笔者认为目前学界的研究局限在于,一方面,尚未全面建立性别史专题研究的历史分期与演变范式,忽视共性,缺乏整体史观;另一方面,受限于断代史的讨论范围,过度强调某时代差异性的独特性,夸大差异性。比如,刘健明《唐代妇女面面观——唐代妇女史中文专著研究述评》(《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针对目前唐代性别史研究种种弊端与不足所提出的尖锐批评。
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性别史的各个断代史之间发展并不平衡。有的传统断代史部分本身具有较高的关注度与研究热度,再加上集中利用新材料带来的学术新增长点,比如唐代出土墓志与敦煌文献、明清档案等,从而出现中国古代性别史仍以唐宋、明清等断代史为大宗的局面,而其他断代史的研究则颇显不足,成果较少,导致性别史的论题缺乏不同断代史、不同历史分期的差异性对比,难以兼顾性别史系统全面发展脉络的整体性与个别时段的独特性。
二、出土文献与性别史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中提出著名的论断:“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第308页)性别史的新视角结合出土文献的新材料,两者的碰撞可以开掘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自19世纪末以来,甲骨文、铜器铭文、简牍与帛书文献、敦煌文献及出土墓志等大量出土文献层出不穷,出土文献不仅有补阙正史之功,而且避免了传世文献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屡遭改易的风险,往往能保留其文本的原始面貌。新兴的性别史研究利用出土文献的新材料,不断构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对于本身缺乏女性材料的性别史研究尤其显得弥足珍贵。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对唐代墓志有关女性文献的研究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按《新唐书》《旧唐书》中纪传及附传共二千六百二十四人,而撰著者多年来集释唐代墓志铭,获得三千五百余张。……唐代墓志人数,多于两《唐书》,……这么巨量的记载已有另一部人物志的分量,其中有关妇女的记载,屡见于墓志里。”另据姚平、焦杰两位学者对唐代女性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女性墓志数量远逾1500篇(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及涉及女性资料的墓志远逾8000余方(焦杰《身份与权利:唐代士族家庭妇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王子今《古代性别研究丛稿》则从所见秦汉简帛文献中涉及妇女的婚姻、家庭、经济财产、医疗等各个方面论题入手,进行了或资料汇编式的整理,或系统深入的讨论与研究。以上均利用出土的新材料,拓宽了各个历史时期性别史的研究空间。
笔者曾关注唐代后妃研究,出土墓志对此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进入传统史学书写的少数女性群体,自西晋陈寿《三国志》始设《后妃传》,然而历代后妃仍多有史传失载的现象。后妃群体的数量,《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序》(中华书局,1959年)引《春秋说》周制有“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之数,依《礼记·昏义》(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古制也有后妃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以唐代为例,盛唐玄宗时期,《新唐书·宦者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唐代289年间共历21位皇帝,但是两唐书《后妃传》仅记录30余位后妃。有关学者如柳夏云通过史料爬梳,新增了122位后妃,其中有24位来自墓志等出土文献,约占五分之一的比例,可见出土墓志对于有关唐代后妃群体的性别史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补充。
关于唐代后妃史书失载的成因,两唐书《后妃传》试图作出一系列的解释。“盖内职御女之列,旧史残缺”(《旧唐书·后妃传下》),男性主导书写的传统历史整体缺乏对古代后妃群体的关注与记录,唐后期的时局因素,以及吸取唐前期后妃过度干政造成朝局混乱的教训,唐后期或长期空缺皇后之位,或不再联姻高门豪族的册后纳妃政策,使得唐后期后妃影响力减弱而史上寂然无名。除了以上诸种成因之外,笔者在参与《唐大诏令集》妃嫔册封文的系年校笺工作中,发现其卷二五《睿宗贵妃豆卢氏等食实封制》一文所封赐的唐睿宗豆卢贵妃,虽属于唐前期高品级的妃嫔,亦不见载于史册。幸而其墓志昭然于世,1992年,河南洛阳南郊出土“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墓志,据此考知,豆卢氏原本是统领后宫的宠妃,却因复杂的内情导致“出内”事件,其作为后妃而长期出内的现象在唐代尚属孤例,这可能是其不见于史载的个体特殊原因,这也是出土墓志补阙正史的一个具体事例。
运用出土的新材料,已成为当今性别史研究的学术主流。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被认为是具有发端性质的代表性成果。其拓展性的学术探索工作方兴未艾,需要不断反思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性别史研究,首要面对和解决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包括易于形成孤证不立、原始文献的学术信息较难挖掘、材料真伪问题等。以唐代墓志为例,前引毛汉光讨论唐代女性墓志一文,曾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事实:“唐代墓志人数,多于两《唐书》,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为独立之资料,并不同于两《唐书》。”此“独立之资料”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可以拓展史实研究材料的广度、丰富度,另一方面又面临一鳞半爪、孤证难立的困境。王国维所论“二重证据法”强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互证,如果缺少这一环,失去传世文献的支撑,出土文献易于沦为孤证。此外,铜器铭文、简牍文书、出土墓志等出土材料的撰写往往具有一定的范式,为亡者、尊者讳,内容表述上的模式化、专业化、过简及避讳等因素,造成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学术信息十分有限,需要深度挖掘。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材料由于年代久远,互证文献缺乏而研究难度增大,甚至有的购买于文物流通市场,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质疑、识别与讨论其真伪的问题。如何充分了解与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自身的特性,对藉由出土新材料进行深入拓展的性别史研究提出了难题与挑战。
此外,性别史框架下的出土材料解读与运用,研究视角容易陷入“性别”的局限与误读。邓小南《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论及一个典型的案例,阿斯塔那高昌虎牙将军张师儿夫妻合葬墓(86TAM386)的发掘报告说明其葬式为“男尸在里,仰身直肢;女尸在外,屈肢葬,侧身面向男尸”。该文对此进行非常审慎的学术思考与判定:“葬式背后可能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男性仰身直肢而女性屈肢葬,显然值得注意。‘解读’这一葬式,需要联系该地区该时段的整体丧葬环境及具体相关资料”,据实地考察,此种女性侧身屈肢的墓葬形式在当地实属绝无仅有的现象,“从该墓的墓志记载看,张师儿死时72岁,其妻则死于99岁,这位夫人很可能因年迈佝偻而只得侧身屈肢入葬;面向其夫则是夫妻关系下的自然选择,而不一定是性别歧视的产物”(第331—332页)。综而论之,为了针对此种“性别意识笼罩一切”的问题进行纠偏,应该建立更为宏阔的研究视野,避免主观误读;同时,应该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与信息,建立多元的史料互证,尽可能地还原客观的历史场景。
诉讼档案、契约文书与明清性别史研究
阿 风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性别史研究方法,特别是社会建构论开始影响到妇女史研究。1975年,纳塔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提出:“我们应该重视研究男女两性各自的历史”“只重视第二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Natalie Zemon Davis, ‘Women's History in Transition: The European Case, ’Feminist Studies 3: 90, 1976)。1986年斯科特提出“性别作为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出性别如同阶级与种族,是一种研究的取向。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在撰写人类的全新历史”(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December 1986)。性别史理论学者常常认为一般历史学家的妇女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传统的社会科学视角的历史研究方法,采用了惯用的公式法则,进行一般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认为这些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性别史研究方法一度被认为是推动妇女史研究,甚至是历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手段。从后来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性别史的方法确实扩展了妇女史研究的思路,除了传统家庭内部男女性别地位研究外,种族、社会阶层、身份地位及教育水平对于妇女地位的影响也受到更多关注,有关才女、列女的文化与文本书写等,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妇女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参见衣若兰《论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多元交织》,《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0期,2017年)。
不过,历史研究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妇女史研究也同样如此。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妇女史研究方法,还是性别史研究方法,是否能够取得研究的突破,对于史料的运用还是非常重要的。2002年,《历史研究》第6期曾组织了“历史·史学与性别”笔谈,发表了多位社会史、妇女史的学者的看法,他们都认识到性别史研究方法对于女性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指出,“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如果“摒弃传统史学的基本功”,“离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就不是史学了”(郭松义《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历史研究应该有坚实的史实作为根据,妇女史由于它的开拓性和史载的零散缺略就更应该做好基础工作。”(高世瑜《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可以说,对于史料的重视是这些学者们的共识。回顾明清妇女史的研究历程,除了性别史研究方法外,民间文献、文书档案的广泛利用、深入挖掘成为推动妇女史研究取得新突破的重要契机。
一、从妇女史到性别史
在20世纪90年代,从性别史的角度研究女性史的重要著作是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斯坦福大学,1994年。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她在该书的“绪论”中指出,“只有借助‘社会性别’这一历史分析范畴,有关她们(闺塾师)生活的文本和她们的语境,才能被充分阐明”,“只有当历史学家对‘五四’文化遗产进行反思时,社会性别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效范畴”,“通过重视社会性别,我们将会发现明末清初的中国是如此的生机勃勃,而这种社会史研究,会为我们业已熟知的历史分期带来修正和调整”(第1页)。换句话说,性别史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妇女史及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最初主要还是针对“五四”妇女史观的一种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对于中国妇女的描述多不脱男尊女卑的格局,“不是将妇女贬为低下卑微,即是悲叹其苦境堪怜,是以妇女史乃成为女性牺牲史”(卓意雯《清代台湾妇女的生活》,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第4页)。中国妇女的历史是“一部被奴役的历史”(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4页)。不过,早在20世纪40年代,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反思“五四”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那些固化的观点。人类学家雷蒙(Raymond Firth)教授1948年在为林耀华《金翅》所写的“引言”中提到:“过去一般人都以为中国的女性是被压迫的人物,她附属于夫家的亲族,和臣服于婆婆之下,几乎只是一件家产而已。但在本书中我们所提到的女子却完全不同:她们是拥有私产而将之投资到生意上的女人;是妯娌争吵、教唆丈夫违抗婆婆的女人;甚至拿刀追赶丈夫而误伤干涉这场风波的长辈的女人”(《金翅——传统中国家庭的社会化过程》,宋和译,桂冠图书出版,2012年修订3版,第4页)。社会学家的成果已经揭示出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另一面。与此同时,法制史学者通过法典、判牍、旧惯调查等史料的分析,认识到在传统的礼法体系中,女性虽然附属于男性,但也有自己的权力空间,特别是寡母在土地交易、分家过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论》,弘文堂,1950年;《中国家族法原理》,创文社,1967年。仁井田陞《中国的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这些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五四”以来妇女史研究中一些固化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有关明清婚姻史、家庭史研究中,除官修正史、方志等史料外,民间文献开始受到广泛重视,这也推动了有关中下阶层妇女的生产、生活与生命研究的深入。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变迁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明清时期族谱为基本素材,运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通过对家族人口的生命统计,作者分析了女性的生命轨迹,指出明清时代,就只结婚一次的丈夫而言,大约有百分之八鳏居30年以上;就不同身份的妇女来看,寡居30年以上的元配有百分之十七,继室有百分之十九,侧室有百分之三十(侧室寡居者比例特别高,当然是因她们的年龄与丈夫相距太大的自然结果)。丈夫平均鳏居的时间1155年,妻妾平均寡居的时间是1694年。所以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认为“明清中国妇女寡居者多而且时间长是不争的事实”(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丛书第十五种,1992年,第56页)。这种利用社会科学方法,通过数据统计而得出的结论相对令人信服。特别是该书对比了男性与女性的生存轨迹,从而与法制史的研究成果相配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法体系中寡母的权利与地位的实态。
这一时期,利用多重史料的综合实态分析成为一种潮流,郭松义研究员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搜集年谱、地方志、文集中有关婚姻、女性的史料,先后撰写了“清代绅士阶层的婚姻行为”“清代的纳妾制度”“清代的节妇、烈女和贞女”多篇论文,分析了上层社会人士的婚姻观。然后同时又利用“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档案及家谱等史料,探讨了中下层民众婚姻观与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2000年,他完成了《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这本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全面地梳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婚姻社会圈、地域圈、婚龄情况,分析了童养媳、入赘、妾及寡妇再嫁、出妻典妻行为,指出在清代,国家一方面通过旌表贞节来维持其所谓“人伦之大、风化最美”的婚姻伦理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广泛存在着与统治者倡导的婚姻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一方面,绅士家庭虽不乏年轻寡妇,甚至有的还不到20岁,却很少有再嫁的情况。而下层妇女守寡后,半数以上都会选择再嫁。有些地方,甚至“夫死鲜守节”,“妇人不以再嫁为耻”。同样,在婚龄方面,也存在着阶层的差异,“大抵富家结婚男早于女,贫家结婚女早于男”。郭著同时结合“刑科题本”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奸情案件,指出当时男女私通属于社会上经常可见、不可忽视的事实。透过郭著细密的研究,可以看出清代中国的伦理与生活的双重性,让我们认识当时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的处境。这些研究实际上就是结合传统史学与性别史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除了女性的家庭角色之外,女性的社会角色也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以明末清初中国经济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才女群体为中心,分析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于男女性别关系的影响。她认为,坊刻的繁荣、女性阅读与创作群体的增加,促进了女性生活的内领域与公众领域的融合与交叉,从而构筑了女性的一个社会文化空间。不过,“女性从家庭生活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取最大自由时,也正是其依靠公众领域的男性程度最高时,正是这些分合的调节机制,促使在社会经济剧变的情况下,社会性别体系得以重新整合,并得以延续”。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稻乡出版社,2002年)以“三姑六婆”这一女性群体为核心,考察了中下层女性与社会的关系。该书从宗教与信仰、医疗与生育、商业与中介三大职业类别勾勒了市井巷陌的中老年妇人的生活样貌,拓展了女性研究的空间。
二、诉讼档案与性别史研究
在明清各种史料中,诉讼档案是比较典型的性别史史料。特别是婚姻奸情类诉讼案卷涉及的多是中下层的人士,而且包含两性双方的供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性别冲突,不仅可以了解女性,也可以了解性别冲突中男性的世界,因此成为近年来有关性别史最重要的史料,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1998年,赖惠敏《情欲与刑罚:清前期犯奸案件的历史解读(1644—1795)》(《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6期,1988年)从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明清档案史料选取了60件有关犯奸案情的案例,通过对于男女职业、身份、地域等方面分析,考察了当时庶民婚姻冲突的实态,并分析了情奸与庶民的经济活动,探讨了庶民的婚姻现象。作者指出,“像寡妇再嫁、童养媳、入赘、养老女婿等,在庶民心里乃习以为常。……这些庶民的婚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隐藏在清代礼教之下部分庶民的生活面貌”。王跃生选取清代乾隆四十六年至六十年间发生的2000多个“婚姻家庭类”个案资料,通过案件当事人供词中的籍贯、年龄、婚姻情况的整理与分析,探讨了当时婚姻各个阶段的冲突,进而分析了当时女性婚姻生活状况(《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美国学者苏成捷(Matthew H.Sommer)《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中译本,谢美裕、尤陈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结合性别史方法,利用诉讼档案研究明清时代的法律与社会。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结合了中央与地方有关奸情类的司法档案,通过律例变化与司法实践的分析,探讨了18世纪的中国,随着雍正时期贱民解放运动的展开而导致身份关系的削弱,社会性别展演模式逐渐取代了以往身份地位展演模式,有关“奸罪”的法条逐渐摆脱了过去的身份等级的因素,新的性别制度跨越了身份界限,采取一致性的性道德和刑事责任标准,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应该遵守婚姻中所定义的性别角色,以维持一种通过使众人皆恪守其家庭角色来加以界定的社会性别秩序。同时,作者通过诉讼档案中涉讼人群的分析,指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清代的司法制度上面,那么便可非常明显地看到精英阶层之外的人们此时处于被关注的中心”,也就是一般的小农、市井小民和各种各样的社会边缘人,有关奸情的法律规定的变化,“可能准确地反映了那些固定居所的小农家庭的家长们感到焦虑和最为关心的问题”(第484—485页)。
该书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雍正时期中国社会身份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良”在法律与观念方面的变化。不过,清朝雍正时期是否是宋代以来中国社会身份转变的重要时期,还需要仔细分析。事实上,从《大明律·户律》中“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这段规定就已经表明身份关系的转变实际上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了(西村かずよ《明代的奴仆》,《东洋史研究》38卷1号,1979年)。高彦颐的研究也表明从明代后期开始,在很多地区就已经发生了社会性别的转变。因此,对于雍正年间的贱民解放运动地位的正确把握,还需要了解明代至清初身份关系变化过程。同时,在传统中国,绅士与庶民虽然存在经济基础与社会地位的不同,但他们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生活理念(吉川幸次郎《支那人の古典とその生活》,岩波书店,1944年)。因此,一方面要考虑到经济基础、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婚姻与家庭生活不同,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相同性,甚至对于贱民阶层,也不能忽视他们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也与庶民,甚至绅士有相同的一面。
在使用诉讼档案时,也要注重这些资料所反映的人群的代表性。事实上,“刑科题本”类的诉讼档案往往都是涉及人命等重大案件,反映的是严重社会冲突的一面,而且多是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所以,包括郭松义、赖惠敏、王跃生等学者也都认识到诉讼档案,特别是“刑科题本”的局限性。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都注意同其他史料的结合,确保结论的普遍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诉讼档案涉讼的人群主要是中下层民众,就认定清代立法存在着一种“小农化”的特征。
三、契约文书与性别史研究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引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的权力理论,指出,“亲属等级制度的外表和官方的权力结构,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际情况”,“即使在中国这样的父权制社会中,亲属关系和家庭体系也不仅仅是男性在运作。女性能够运作权力的性质和程度,不仅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肩负的使命,也取决于其他主观因素,如她的个人技巧和她在生命周期的位置”(中文版,第15—16页)。而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传统中国妇女礼法与生活的这种双重特点的史料,就是契约文书(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下面引用《明弘治十三年(1500)祁门谢阿汪(汪氏希仙)立〈标书文簿〉》(《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五,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分析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权力运作情况。分家书序言中这样写道:
旸源谢阿汪,名希仙,相潭汪舍芳女,长配旸源谢永达为妻,生有二男三女。有夫于成化辛卯年不幸病故,遗下贰男,长以洪,年方一十六岁,次以明,年八岁。三女,长云英,次惜英、华英,俱幼。所有家务一应等项,俱索己身,只得挣揣,男婚女嫁。今幸不堕先志,家抵有成,承祖分授田租约有肆佰叁拾余秤,夫续置田租贰佰柒拾余秤。夫故后,是男以洪卓立,将众财物续置田租约有贰佰陆拾秤,共计荒熟田拾亩零。其契字是以洪名目,今俱载标书内分讫。其契字是以洪收掌,要用之日,毋许执匿。外有男以洪、以明各自妻财己置田地山场土名处所,并听己业,贰男毋许异言争论。今男女成行,本身年老衰倦,家务重大,不能管顾,于弘治六年间命贰男分爨各膳已讫。今凭婿余景等将户下田地山塘,肥硗登答,均分为贰,写立孝、弟二字簿扇,一样二本,各阄一本。已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管业。其未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同共对半均业。其一应山场田地,及竹园并漏落,不及逐一开写,并系对半均业。所有本户税粮,除贰男己买田山税粮自收自纳外,其余税粮不以民庄荒熟并亩步多寡为拘,并系对半均纳。所有已分并未分田地山场,倘有屋基风水,俱系众用,毋许独占。再议,拨换贰男己买田山地内若有风水,不在其内。自摽之后,二男各要遵守,毋许异言争论。如违,准不孝论罪,仍依此摽书为准。呜呼!噫嘘!汝父早丧,汝母孀居,上有公姑,下有子女,养生送死,辛苦百端,嫁女婚男,劬劳万状,兴言及此,痛裂心田。汝等当以母心为心,毋忽毋怠,故嘱!故嘱!
分家书的序言往往就是一部家庭简史,而且作为法律文书,其中涉及家庭情况、产权关系的内容也相对真实。其与《列女传》等具有“制作生产”的传记书写(参照衣若兰《论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多元交织》)还是有所不同。正如刘翠溶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明清中国女性守寡时间长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所以当父亲去世、诸子成年后,母亲主持分家也成为自然的选择,这也符合律法要求尊长“许令分析”的规定。现存的分家书很多是母亲主持分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件由寡母主持的分家书中,登录的田地山塘等财产的清单就达25页,可以看出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在分家序言中,立书人谢阿汪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亲属关系,她本名汪希仙,是相潭汪舍芳的女儿,长大后嫁给旸源谢永达。可以知道女性在本家冠父姓,出嫁后冠夫姓,这实际上就体现出“在家从父,既嫁从夫”的礼法原则。谢阿汪之夫谢永达于成化七年病故,当时其长男谢以洪才16岁,次男以明只有8岁,这是一个母寡子幼家庭,“上有公姑,下有子女”,寡母谢阿汪承担了家庭的主要责任,包括公姑的“养生送死”,子女的婚嫁,可以说“辛苦百端”“劬劳万状”。
虽然是母亲主持家庭事务,但按照明代户籍赋役制度,有子寡妻不能以女性名义立户,所以涉及土地购买等,只能是以儿子的名义,儿子是户籍上“户主”,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夫死从子”的原则。这件分家书明确说明丈夫去世后,购买土地,“其契字是以洪名目,今俱载标书内分讫。其契字是以洪收掌,要用之日,毋许执匿”。以长子名义购置的土地不是他个人及其小家庭的财产,而是母子共居家庭的共同财产,分家时必须均分。同时,分家书中明确规定“妻财”置到财产为各个小家庭所有,不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处置,这也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件分家书最后虽然署名“谢阿汪”,但谢阿汪没有手写花押,而是押有“汪氏希仙”的墨印戳记一颗,这是目前笔者仅见的明代唯一的女性使用戳记代替花押的分家书,而且戳记中刻印是冠以父姓的本名,与冠以夫姓的“署名”并不一致。同时,簿册每页中缝下部押有“汪氏希仙”朱印戳记一颗,这种骑缝戳记与当时乡村职役戳记押于各种赋役、土地册籍的性质相同,是母亲对于分家书的“认证”。从戳记可以看出,谢阿汪事实上主持了家里的各种内外事务。
通过这件分家书,可以看出当时伦理与生活的双重性。一方面,女性出嫁要冠夫姓,女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土地,这是一种礼法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寡母代替丈夫主持家业,包括男婚女嫁、家产增殖、家产分析等实际上都是由谢阿汪来操持。因此,这件分家书中的谢阿汪实际上就是父权制社会中妇女通过个人的能力,维持了整个家庭的生存,展示出一位有能力女性的一个生动实例。
不过,传统中国社会,不是以个人为起点,而是以家庭为起点。岸本美绪在谈到中国家产所有权主体时指出,在中国作为所有主体的“人”,“是作为人伦关系网中一个结点的‘人’。家长涵摄着子孙人格的同时,家长的人格也被涵摄在亡故祖先的人格之中”(《买卖土地与买卖人口——围绕“所有”的比较的尝试》,原刊2004年,中译本见氏著《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因此,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制度设计中都与家庭的代表——“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在一定情况下,女性可能起着主动、甚至重要的作用,但在制度框架中,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亲属制度之外发挥作用。因此,对于家产的分割,仍然要遵循着诸子均分这种基本的原则,包括购买土地财产,也要以长子为主。女性的能动性仍然被限制在家庭的法律体系之中,并没有因为个人能力而改变整个伦理关系与制度规定。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史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各种所谓的“语言转向”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特别是性别史研究者强调性别的“社会构建”,这也会给人一种印象:“文本或书写之外,现实并不存在。”一些人担心,“这种新的历史会走向相对主义的深渊”。因此,有一些性别史的学者试图形成“中间路线”,在汲取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的同时,仍然从传统史学中吸收分析工具,将运用话语分析的文化史和社会历史方法结合起来,理解它们的社会与历史背景(Sonya O. Rose, What is Gender History?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2010. 索尼娅·罗斯《什么是性别史》,曹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03—108页)。这种结合传统史学方法的性别史研究可能更具有“历史主义”,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将性别史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一直是妇女史研究的主流。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社会学者、法学者就已经开始反思“五四”妇女史观。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族谱、女性文集、契约文书、诉讼档案等新史料的广泛运用,对于不同史料的综合实态分析,包括刘翠溶、郭松义及高彦颐、苏成捷等学者的研究,事实上都是结合了性别史与传统史学方法。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社会性别看待妇女的地位,而且能够为性别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实现了性别史的研究目标。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借鉴多元交织理论,对于各种史料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思考各种身份认同的支配与建构,“将性别独立出来与多种不同的身份(因素)交会观察,并且发展中华文化自身脉络的交织变项,尝试描绘立体动态的交织图像,或许才有助于中国性别史的进一步发展”(衣若兰《论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多元交织》)。
食与色:食谱与中国性别史研究
奚丽芳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中国的妇女史/性别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大量论著面世。但总体看来,对“食物”这一要素关注不足。不过,近十几年来,食物史研究已成为热点。尽管历史时期妇女在家庭烹饪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但有关“食物”的史学论著却很少关注女性的角色,对妇女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未见深入的探讨。本文检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食物与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分析既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文章以食谱与中国性别史研究为例,探讨“食物”与中国性别史研究的可能性结合,展示“食物”这一独特视角对于性别史研究的意义。
一、引言
若以“食物与性别”视角审视既往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关注到历史时期饮食结构的性别差异、妇女的家庭食物工作及男子的饮食书写等问题。周立刚《举箸观史:东周到汉代中原先民食谱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借助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从食谱(人群食物结构)特征的角度观察社会变革之下东周和汉代先民的日常生活。该书对食谱特征的考察视角涉及不同阶级与时代、城乡与性别差异等。尽管对于食谱特征的性别差异着墨不多,但这种讨论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性别与社会地位或者分工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思路。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部分章节描述满族妇女如何保存蔬菜及烹饪肉类食物,指出满族妇女学习借鉴汉族主妇的方法制作家常菜,同时也保留了满族人特有的饮食口味和喜好。岳立松《饮食男女:清代忆语文学的饮食书写》(《新疆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认为,忆语的饮食书写流露出明清文人的饮食品味及生活情趣,建构起夫唱妇随的合乎男性才子期许的女子形象。尽管该文以文学作品作为写作材料,但忆语文学是男性文人记录闺房情态、婚恋生活及日常饮食等家庭生活的一种写作方式,因此具备史料价值。这些论著将饮食与“男女”的社会属性作关联研究,以“食”为线索描写女性生活与性别角色,但缺少跨学科意义的系统性与逻辑性的论证。
“食物与性别”视角下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性别。这些作品以性别视角探索食物及食物文化,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关系、权力与身份等问题。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考古人类学刊》第67期,2007年)从台中县大甲地区妇女与饮食的访谈资料出发,利用中医文献追究养生饮食之历史成因。作者选择经常被妇女食用的当归,说明食物会被文化设计成包含男女价值差异的物品。该文指出,在男女自我的性别认知过程中,食物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媒介。此外,近当代人的相关成果也时有出现,拓宽了妇女史的研究领域。
综上,“食物与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史研究作品不多,相关作品在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饮食生活中,男女两性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何不同?食物工作中,男女如何分工?在记录饮食体验及烹调经验时,男女两性是否会有不同着眼点?既往研究很少探讨这些问题。以“食”为线索研究性别角色、性别分工与女性地位等问题的严肃学术专著十分罕见,无论是食物史研究者还是性别史研究者,很少在主观上意识到“食物与性别”这一跨学科视角对中国史研究领域拓展的意义。
二、历史时期的食谱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观察,所谓食谱,“是以文字记载食物烹调与制作的方法”。食谱可以包括以食经、食单、菜谱等名称命名的文本。食谱兴于魏晋六朝,“《隋书·经籍志》将食谱分别置于‘诸子略’的农家类,与‘方技略’的医方类之中”,不过这些食谱大多亡佚,只有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保存不少已佚食谱的原文,其书中“烹饪资料多取自崔浩《食经》”,因此崔氏之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饮馔之书”(逯耀东《明清时期的文人食谱》,《中外文学》第31卷第3期,2002年,第27—30页)。流传至今的内容完整的食谱基本是宋代及其后出现的,明清时期尤多。改革开放以来,食谱的编写出版迎来了高峰时期。
若是从食谱撰写者的性别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前现代食谱皆为男性文人所撰,女性撰写流传的食谱屈指可数,作者相对明确的女性撰写的食谱只有《吴氏中馈录》与晚清曾懿《中馈录》。所以历史时期的食谱,其作者的性别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这样的性别特征在食谱的内容方面也有彰显。女性为作者的食谱,内容具体,具有日常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女性是“中馈”事务的实践者,因此,也就具备了撰写食谱的天然优势。《吴氏中馈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共收入70余种菜点制作方法,包括脯鲊、蔬食及甜食的制作方法和技巧。其菜点名录包含很多预制食品,可以有效节省一日三餐的准备时间,有助于女子经济管理家庭饮食。曾懿《中馈录》主要由“中馈总论”和“二十节”食品制作和保藏方法组成。“二十节”的内容包括制宣威火腿法、制肉松法、制五香熏鱼法、制醉蟹法、制辣豆瓣法、制腐乳法、制酱油法、制泡盐菜法、制酥月饼法等。通过这些方法制作的食品具有家常的特点。曾懿在“中馈总论”中阐述了自己的饮食理念及《中馈录》的价值,她引述《论语·乡党》的经典论述说明《中馈录》跟孔子的饮食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她最后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希望《中馈录》有助于实现“节用卫生”的目标(曾懿《中馈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第1—2页)。不过,“节用卫生”理念的最终指向仍然是实用性与日常性。
而男性则是中馈事务的旁观者,其撰写食谱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主中馈者”认知、其他厨者经验或前人饮食典籍中的食事书写。宋诩在《宋氏养生部》(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第2—3页)中指出他撰写食谱的初衷是为了记录他母亲辗转各地所习得的饮食烹饪经验,而这一过程是经由其母亲“口传心授”而实现的。屠隆为高濂《遵生八笺》(王大淳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页)一书撰写序言时提及高濂的“咨访道术”与“家世藏书”。“咨访道术”的寓意可能包含作者搜集秘方或私家食谱,或在游历、宴饮活动中加以关注;“家世藏书”意味着《遵生八笺》的撰写参考了众多藏书资料。
男性食谱所展示的饮食理念相比女性食谱更为丰富。高濂《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指出:“饮食,活人之本也。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血气盛,血气盛则筋力强”(第725页),把饮食之事与阴阳五行学说及养气理论相联系。顾仲《养小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第10页)指出饮食应当关注清洁与五味得宜的问题:“饮食之道,关乎性命,治之之要,惟洁惟宜。宜者,五味得宜,生熟合节,难以备陈。至于洁乃大纲矣。”龙遵叙《饮食绅言》(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第189页)提出了通过节俭以达到养德、养寿、养神、养气的目的。李调元在整理其父李化楠《醒园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第2—3页)时作序指出,“夫饮食非细故也”,认为饮食并不是一件微贱之事。袁枚《随园食单》(乾隆五十七年小仓山房藏本,第1页)视饮食之道为学问和艺术:“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从男性所秉持的饮食理念可以推知其书写目的还包括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
历史时期食谱的受众也有性别的差异。女性撰写的食谱,其预想的受众主要是女性。民国以前由女性撰写的食谱《吴氏中馈录》与曾懿《中馈录》都以“中馈录”作为书名,这种命名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食谱撰写的目的在于为妇女主持中馈提供参照。曾懿在《中馈录》中明确指出其撰写目的是为了让初学饮食烹饪的女子能够以此作为依据,承担主持家庭饮食事务的责任。她在食谱中将“主中馈”描述为女性的家庭责任,说明她认为烹饪是妻子职责和作为一个女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食谱不仅成为女性实践主流社会性别角色的证明,也成为其传承这一性别角色的重要途径。
而男性撰写食谱并不为“主中馈”服务,并且,这些食谱的受众往往也包括同为男性的各类文人,故而在文本的书写上字斟句酌,讲究文字技巧。巫仁恕《明清饮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与品味塑造——以饮膳书籍与食谱为中心的探讨》(《中国饮食文化》第2卷第2期,2006年)所提出的“文人化食谱”,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男性食谱书写的特点。
男性文人在撰写食谱时往往关注饮食道德与伦理,认为饮食是民生大事。他们更加关注食物形而上的文化意义,更看重食谱的超越性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男性食谱也有落实和传承主流社会男性性别角色的特点。
三、食谱与中国性别史研究
(一)食谱与中国帝制时期男性的研究。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食谱是由男性文人撰写的,因此既往有关食谱的研究大多反映的也是历史时期男性群体的生活,与男性的性别角色。
食谱有助于饮食实践,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有其他用途——像其他类型的文本一样,食谱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社会交往和构建身份认同的方式。陈元朋《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家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察》(《中国饮食文化》第3卷第1期,2007年,第40页)认为,林洪将日常饮食名之为“清供”,是想借此来突显自身的品位:“与饮食相关的‘清’之议题,不论是涉及思想层面较多的‘清供’,又或是与身体感知发生较密切联系的‘清味’,似乎都与两宋以降蓬勃发展的士流文化难脱关联。”魏琛琳《聚焦饮食书写:李渔的矛盾性及个人独特性》(《河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以《闲情偶寄·饮馔部》为主要材料探讨李渔饮食书写中所体现的“士”“民”身份交叉的复杂性与个体独特性。而王标《美食中的友情——〈随园食单〉人物考》(《中国饮食文化》第5卷第2期,2009年)统计《随园食单》收录的327种食谱当中出现的115处人名或店名,按照人物社会背景进行归类和考证,指出食谱总共涉及80个人和17家店铺。从称谓上看,有制军、中丞、方伯、观察、太守、明府,甚至有僧人、尼姑、道士、厨子,三教九流皆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枚的广泛交游。
食谱是构成编撰者文人身份的载体。张光直(K. C. Chang)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1)认为,前现代文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饮食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巫仁恕《明清饮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与品味塑造——以饮膳书籍与食谱为中心的探讨》通过分析明清的饮膳书籍与食谱指出,“明清部分士人或文人为宣扬自己特殊的味觉观,创作出一种特殊风格的文人化食谱,其实就是以选择性的摄食来表达自己的‘品味’,并建构他们社群的自我认同,以利于和其他社会群体作区分”(第45—46页)。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 ‘The Obsessive Gourmet: Zhang Dai on Food and Drink,' In Issac Yue and Siufu Tang,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1)认为,文人们通过烹饪著作定义“好品味”巩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炫耀了自己的美德。维维恩·罗(Vivienne Lo)和佩内洛普·巴雷特(Penelope Barrett)‘Cooking up Fine Remedies: On the Culinary Aesthetic in a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Materia Medica’(Medical History, Vol.49, 2005, p.403)指出,“除了实用性之外,这些饮食书籍还可以作为改善精英生活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像绘画和诗歌一样,出于与时空相关的怀旧原因而受到喜爱,暗示读者和收藏家们丰富的行旅经历与文化积淀以美化受过教育的话语,或确保精英血统和传统的连续性”。
由上可见,既往以食谱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或者以食谱作为史料的成果,关注食谱的社会文化价值。他们的研究指出历史时期很多文人以对食谱的拥有来建构文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品位。尽管既往研究成果中的史料——食谱都由男性文人撰写并且客观上揭示了男性群体的社会生活状态,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在主观上意识到性别视角下的食谱分析所可能带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上的突破。
(二)食谱与女性研究。目前可见的民国以前的食谱大多由男性编撰,食谱书写过程呈现出了性别特色,但是目前有关食谱的研究成果并未关注书写者的性别区分。鉴于这种现状,笔者曾经分析曾懿《中馈录》在内容、架构及饮食理念等方面的特点,以此对比男性食谱撰写及《吴氏中馈录》的写作特色,分析曾懿作为女性的饮食书写的特色及对于“主中馈”的态度,进而探讨晚清这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由“主中馈”到尝试饮食书写的过程所反映的女性跨越家庭内外的变化过程。
曾懿在《中馈录》中强调妇人“主中馈”的职责。但是梳理历史时期男性撰写的食谱可见,男性未曾强调食谱充当指导“中馈”实践的作用。前文已经提到,男性是“中馈”事务的旁观者,其食谱撰写更加关注食物的功能与文化意义。而女性,她们是“中馈”事务的实践者,认可“妇主中馈”的家庭分工模式,在食谱书写中秉持“主中馈”目的。不过,民国以后女性更多地参与了食谱撰写,并且她们基本不再强调“主中馈”目的。比如《中国食谱》(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24页)的作者杨步伟对于“中馈”之事表现出抗拒之意,从小认为“淑女不应下厨”,“一向看低做饭这事”。分析历史时期男女两性的食谱撰写,探讨各自不同的书写内容与目的,进而分析不同的书写特色如何呈现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这是今后研究中可以选用的视角。
(三)食谱与性别关系的研究。历史时期的食谱大多由男性书写,因此也形成了男性广泛的社交关系。李调元整理其父李化楠《醒园录》搜集的饮食烹饪手稿时写道:“先大夫自诸生时,疏食菜羹,不求安饱。然事先大父母,必备极甘旨。至于宦游所到,多吴羹酸苦之乡。厨人进而甘焉者,随访而志诸册,不假抄胥,手自缮写,盖历数十年如一日矣”(第1页)。李调元之父做官游历各地时,每遇美味佳肴,就向厨师请教,然后将烹制方法记录在案。清中叶美食家袁枚所撰写的《随园食单》“记食谱三百二十七种,前后出现了一百一十五处人名或店名,共涉及八十个人和十七家店铺”(王标《美食中的友情——〈随园食单〉人物考》,第49页)。王标的研究已经关注到“美食中的友情”,但是并未探讨这种社交活动中的性别因素。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思考,这种因为食谱书写所形成的社交关系与诗词圈或者书画圈的社交相比,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区别?这种因食谱书写所形成的男性社交与女性社交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对于食谱的研究也有利于观察男性与女性的交流互动。崔浩在《食经叙》中指出,“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827页)。可以说,《食经》一书是崔浩根据母亲口传心授而写成的。这种食谱撰写方式并非个案,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宋氏养生部》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撰写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儿子的男性与作为母亲的女性在食谱撰写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既往关于食谱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食谱的史料价值并且关注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历史时期绝大多数的食谱都是由男性文人编撰的,男性食谱与女性食谱呈现出了不同特色。食谱生动地展示了“食物”和性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值得性别研究者关注。
四、结语
利用食谱这种“食物”要素,开展性别角色与性别分工等研究,可以拓宽性别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古代中国留存了大量食谱,而时至现代社会,食谱更是浩如烟海,因此中国社会具备以食谱为视角进行性别史研究的客观条件。从食谱书写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食谱大多由男性书写;若是关注性别分工,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妇主中馈”现象见于众多史料记载之中,目前可见的女教书、家训,笔记文集中墓志铭、祭悼文、行状等史料涉及大量“中馈”论述。因此,以“食谱”作为性别研究的对象与材料,值得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投入精力积极探索。
对“食物”的研究有助于发展近年来在性别史研究中引起重大兴趣的领域,性别史研究也有利于拓展食物的物质和情感维度。研究者认为,几乎所有文化中的男性和女性都与特定的食物和控制其消费的规则有关,食物是一种分化的手段,也是一种联系的渠道。一个社会可以通过男女获得和控制食物来分配或剥夺他们的权力,男人和女人生产、提供、分配和消费食物的能力是衡量他们权力的关键(Carole M. Counihan and Steven L. Kaplan, eds. Food and Gender: Identity and Power,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pp.1-2)。在传统的家庭食事性别分工的角色要求下,女性必须充分考虑和周全处理与食物相关的所有事务。对帝制时期的中国妇女来说,自我与食物关系的社会设定可谓根深蒂固。即使对现代女性来说,这种联系仍然很牢固。“食物”与性别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价值,这种研究不仅详细说明了妇女在食物采购和准备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而且确定了妇女的优先事项和需要如何挑战在社会和政治上执行的现行价值体系。
END
原文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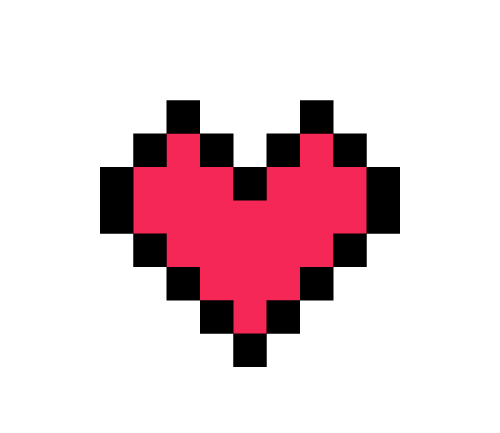 点击图片 订购期刊
点击图片 订购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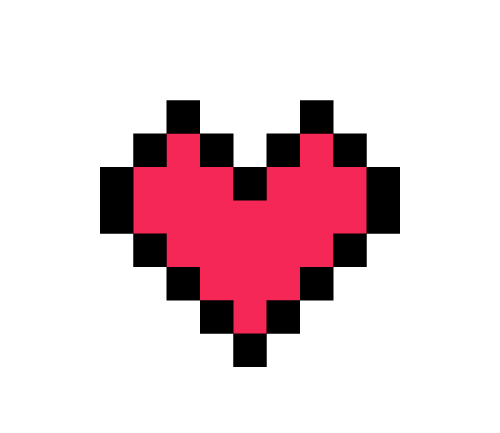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投稿网址:http://zgsyjdt.ajcass.org
1979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本刊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介绍海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前沿及相关信息,以供海内外研究者参考,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主要栏目有:述评·专论、笔谈、专题访谈、批评与反思、海外汉学、会议综述、名家序跋、书评书讯。
实习编辑:晨阳
校对:雨璇
审核:振华